若无“天下”型定居文明,诸子百家恐怕不会出现
【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文扬】
上一篇写道,周朝早期通过宗法分封和武装殖民,在中原大地上实现了第一次的定居农耕文明大一统。这应该被确定为世界政治发展史的一个跨越,因为与同时期世界其他文明大为不同的是,周朝大一统局面的形成,依靠了一种“德治天下”的政治策略。
“德治”的由来
文明各有起源,起源于“多元一体”的定居,还是起源于单一部族的迁徙或征战,区别重大,因为这直接决定了后世关于其部族始祖的类型想象。中华始祖的类型很特殊,虽然也照例被尊为战神,但另一个更重要的面貌,则是指导万民在自己土地上生活的圣王。
中国人作史,按“三皇五帝三王”的顺序,始祖是“三皇”,曰太昊伏羲氏、炎帝神农氏、黄帝有熊氏。“皇”字的古义是“德冒天下谓之皇”,本身就含有全天下至德之人的意思。据传说,伏羲氏教人民作网罟以佃以渔,养六畜以充庖厨,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通媒妁以重人伦之本;神农氏教人民因天时,相地宜,制耒耜,蓺五谷,尝百草,立医道,列廛于国,日中为市,交易而退,各得其所;黄帝有熊氏教人民探五行之情,占斗纲所建,造历法,作算数,为文章以表贵贱,作舟车以济不通,画野分州,设立井田,左右大监监于万国,远夷之国莫不入贡。【1】

:
河南新郑轩辕黄帝像
考察圣王们这些事功,可以看出,无不是定居农耕区内的农业革命活动,今天的话叫“改善民生”,而且是关于全天下人的民生。这当然就是一种至德。对比一下,古代以色列人的圣经叙事讲述的是部族的大迁徙,古代希腊人的荷马史诗讲述的是特洛伊战争,都属于前定居、非定居文明中的行为,充斥着远征、烧杀、抢夺、复仇之类的情节,看不到“天下平”“万国和”的景象,当然也就谈不上德行、德治的问题。
那时世界不通,中国和地中海世界之间没有交流,如果有的话,无论是古希伯来还是古希腊,也必定逃不出蛮夷戎狄的定位,有多少华丽的长诗流传也没用。因为率领部族迁徙或率领军队征伐的英雄,在古代世界随处可见,大地上无数的蛮族游团,每个都有自己的亚伯拉罕、摩西、阿伽门农和阿基琉斯,故事甚至更精彩,区别仅在于有没有留下文字记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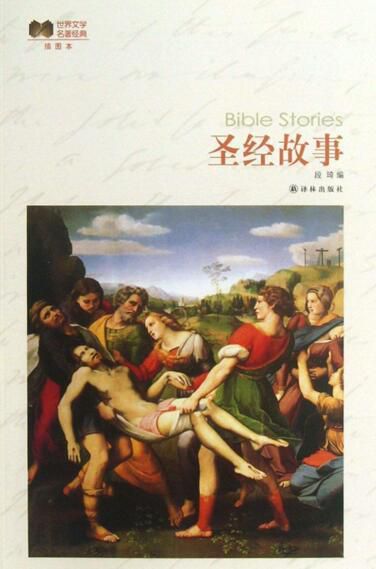
圣经故事
但可以断定,并不是每个部族都能出现自己的伏羲氏、神农氏和有熊氏,因为这些最早的农民领袖和农业革命带头人,都是大有功于天下万民的圣王,只属于“天下”型定居文明,只可能在中华大地上出现。
德治,中华政治的这个核心概念,就是从这里出来的。换言之,中国人所谓“德治”,其实是专属于定居农耕文明的一种道德化政治,不能说最好或最高,但却是最适合于“天下”型定居文明的早期发展的。
中华大地上最早的定居农耕文明区,犹如大海中散布的群岛,被无数蛮夷游团所包围。而之所以能够像星星之火一样,不仅生存了下来,而且终成燎原之势,发展成世界上最大的“天下”型定居文明,一整套适合于定居文明的“德治”,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周朝的早期历史就是一部“德治”的成功史。据《周本纪》,周人先祖后稷“好耕农,相地之宜,宜谷者稼穑焉,民皆则之”,本是一个定居农耕部族中的圣王。但是儿子不窋不务正业,放弃了农耕,“窜居戎狄之间”。好在第三代孙子公刘很有作为,又率领部族在戎狄之间的豳地复修后稷的稼穑旧业。然而农耕事业并不顺利,因为周围的“薰鬻戎狄攻之”。结果不用说,弯腰种地的肯定是打不过骑马打猎的,就这样进进退退纠缠了有一千年。到了古公亶父当政,为了复修后稷公刘之业,终于下决心举国离开豳地,渡漆沮,逾梁山,止于岐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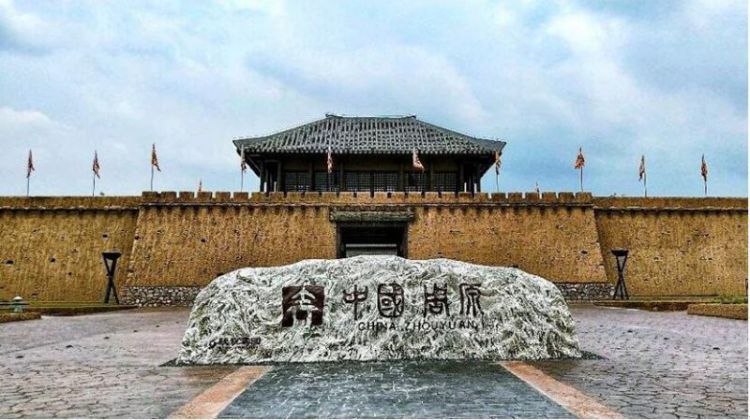
今日岐下周原
审看这段历史,从战术上讲,肯定是周人败了,薰鬻胜了,因为前者被后者赶跑了,丢了豳地。但是从战略上讲,却正好相反,因为周人撤离时,“豳人举国扶老携幼,尽归古公于岐下。及他旁国,闻古公贤,亦多归之”,最后不仅重建了新的根据地、扩大了地盘,而且尽收民心。到了古公之子王季、之孙西伯,“修古公遗道,笃于仁义,诸侯顺之”。周家八百年王业,自文王始。
在公元前一千纪的那个世界,其他地方有没有可能发生类似的故事,大可怀疑。军事上的失败者反而成了文化上的胜利者,凭着仁义二字最终赢了全天下,这样的“德治天下”叙事,遍读其他民族的史诗,恐怕找不到第二家。
后人纪念文王,全都是动人故事——敬老慈幼,礼贤下士,耕者让衅,民俗让长,修德行善,发政施仁,泽及枯骨…盖人心至是已去商而归周矣,“德治”大胜。但这里似乎有个问题:周人这些道德观念和行为到底是如何产生的呢?真的是头脑中聪明智慧灵光一闪的产物吗?设想一下,假如周人没有离开豳地南下关中平原,“德治”能够在北方的薰鬻戎狄当中产生同样的效果吗?能够让周围的蛮族游团像中原的殷商诸侯一样纷纷归附吗?
绝无可能。不要说当时的薰鬻戎狄,从那时起到后来的匈奴、五胡、突厥……直到两千多年后蒙古诸部,这些北方游牧-游猎民族只要不进入中原的定居文明圈,就不知“德治”为何物。他们不仅不会因“德治”所归顺,反而毫不犹豫且理直气壮地一次次越过长城碾压整个中原乃至南方。为什么?归根结底,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道德标准,周朝的“德治天下”只能在定居农耕文明为主的区域内起作用,而在游牧游猎文明为主的区域内,基本没用。
敬老慈幼在定居文明中是美德,但在游牧文明中却不是,因为根本没条件,整个部落必须不断地长途迁徙甚至快速奔走,不可能因为要照顾少数老人,影响整个群体的机动性。恭敬守礼在定居文明中是美德,但在游牧文明中也不是,在马背上生活的所有男人必须以好斗、残暴、贪婪和好色为基本品质,才能让整个群体获得更多的猎物并且更快地繁衍。
一条条考察下来,在定居文明中一直被视为理所当然的那些道德行为,在游牧文明中也许恰恰是非道德,因为不能促进群体的生存发展利益。周文王礼贤下士,尊八十岁的吕望为太公,因为贤士们头脑中的一个良策,就可能大大推进治国平天下的事业。但游牧民族的世界就是茫茫大草原,散落着无数的野兽群体和异族部落,要想生存下来就要尽可能多地消灭它们,因此,计谋远远顶不上勇猛,智力不能代替臂力,与其礼贤下士还不如锤炼战士。
就是这样。若没有大面积定居农耕区、大规模定居农民人口,再出一百个周文王也没用。周人从豳地举国迁徙到岐下周原,从地理上看就是跨越了农-牧分界的400毫米降水线,融进了定居农耕的核心区;从历史上看就是汇入了当时的农业革命浪潮,顺应了定居农耕区的大一统趋势。“德治天下”政治策略的成功,当然要归功于文武周公这些开国者的伟大政治实践,但背后的深层历史运动,却是那个历史时期定居农耕区域的迅速扩大和对周围游牧-游猎蛮族游团的大量吸收。
先秦诸子都在争论什么?
与定居农耕区大一统趋势发生的同时,是一个堪称政治奇迹的新事物的出现——原本作为地理概念的“天下”,通过“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制度安排和“德治天下”政治策略的实行,成了一个地理、政治和伦理的“三位一体”。
天下,同时意味着全部土地、全体人民和全局秩序,天道、人伦和天人相与之际三合一,世界上再也找不出第二个类似的“三位一体”。
早周其时,封王所到之地,新城拔地而起。以周文王为源头,在全天下制邑立宗,每个城市自始封者开始别子为祖,建立宗庙,下一代则按嫡长子继承制再继别为宗。一切都井然有序,各就各位,各得其所。
重要的是,当人为制定的宗法制度遍行于全天下,各地的宗庙都只祭人祖不祭鬼神之后,关于天的观念也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研究者们注意到,在讲述周人迁徙故事的《诗•皇矣》等篇章中,天还是一个被称为“帝”的人格神,“皇矣上帝,临下有赫,监观四方,求民之莫”,像极了希伯来《旧约》中的耶和华;而到了较晚的《书•吕刑》等篇章中,天即变成了“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的抽象物,与人为秩序合二为一了。梁启超对此总结道:
其所谓天者,已渐由宗教的意味变为哲学的意味。而后世一切政治思想之总根核,即从比发轫。【2】
天,不再是任意的、绝对的、超越于人的,而成了规则的、相对的、与人合一的。如《诗•烝民》的表达,上天与万民直接联系在了一起:
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
对这句话,孟子的解释是:“有物必有则,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彝指法度、常规;懿是美好的意思;万民只要遵从天的法则,就是好的德行。梁启超的解释是:
凡一切现象,皆各有其当然之法则,而人类所秉之以为常也。故人类社会唯一之义务在“顺帝之则”(《皇矣》)。【3】
中国人研究六经,往往带着一种想当然,认为天就是天,民就是民,不用多解释,全世界都一样,基本上可以等同于人类社会。其实这是个大谬。在中国人开始将“天”与“民”连在一起,甚至有了“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畏”这类思想的当时,在世界其他民族当中,无论是天的观念,还是民的观念,都还远远没有成型。

《千里江山图》局部
在中国的“天下”型定居文明之外,满眼荒蛮:欧亚内陆的游牧民族长期挣扎在生存线上,为寻找水草和猎物而四处奔走,观念上摆脱不了野兽崇拜的蒙昧阶段。地中海一带的城邦民族则永远被不同的敌国所包围,相互攻伐,从不知“天下”的范围有多大,自然不会形成“天下”观。印度有较大规模的定居农耕区,但却始终没能形成一个与中国类似的“同心圆”或“同心方”地缘格局,无法让定居文明成为一个整体以抵抗北方蛮族的频频入侵,当然也就不成“天下”。至于西欧,作为一个文明它在这个时期还根本没有出现。
所以,当中国的先秦诸子们使用“天”和“民”这两个概念时,两者本质上是一对,是一枚硬币之两面。硬币就是“天下”型定居文明本身,这个文明的一面是生养万物的天,另一面是顺天之则的民。那些不在“天下”型定居文明中的民,要么是蛮族暴民,要么是小城寡民,要么是奴隶草民,皆非“天民”。
“天民”观念最圆满的表达,在《书•皐陶谟》中:
…天工,人其代之,天叙有典,敕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礼,自我五礼有庸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
至此,从“多元一体”定居文明开始,到“天道”哲学的确立,一个独立的、完整的、自洽的天-地-人体系终于出现在中华大地上,并且从此屹立千秋。
独立的,因为一切都起源于中华大地上独一无二的“天下”型定居文明;完整的,因为正是基于这种文明,才有了集合在“天下”概念之中的地理、政治和伦理“三位一体”;自洽的,因为“天下”中的天是哲学意味的天,所以“顺帝之则”就成了“顺天之则”,继而通过“天生德于予”又进一步融化成为人的道德义务,完成“天人合一”。
其他文明中不可能诞生类似的体系。仅仅从人格神到抽象的天这一步,就都没能完成跨越,更不要说“天下”观念的“三位一体”和“天民”的“一体两面”。

儒家六经
然而,凡事都有两面,正如近现代学者反思中华文明时普遍认为的,这个文明的确过于超前和早熟。回看中华历史,无论是“三位一体”的“天下”还是“一体两面”的“天民”,其实更多的只是士大夫们头脑中的理想,而非真正的社会现实。周初“协和万邦”“德治天下”策略的实行,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就建成一个理想社会。虽说从理论上讲,当时的中国农民已初步具有了辜鸿铭所说的“良民宗教”精神,但实际上,在当时的中原地区,游牧的蛮族暴民、城邦的小国寡民、底层的奴隶草民,也都大量存在,与其他文明无异。人毕竟是人,性恶就是性恶,不可能因为《诗》《书》中几句虚无缥缈的哲言,全体农民就都集体升华成了与众不同的“天民”。
历史见证,短暂的“成康之治”过后,“周道衰废”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昭王伐楚不返,厉王侈傲弭谤,再经骊山之耻、平王东迁,诸侯并起礼崩乐坏的局面已成。读书人们心目中那个空中楼阁般的“天下”自此土崩瓦解,于是喧哗四起,众声鼎沸,中华文明最为光彩夺目的思想文化之花大绽放时期随之到来。
70年对话5000年,今天的人们在重读先秦经典时,既不能将它们仅仅看成是圣贤们高人一等的聪明智慧,也不能盲目认为其中的名句格言一如既往地英明正确。大体而言,它们只是“天下”型定居文明这个特殊文明的产物,且生发于这个文明遭遇到理想与现实、超前与滞后、早熟与晚成之间巨大冲突的那个特殊时代。而诸子百家的不同学说,就其实质而言,就是面对这些冲突的诸种不同回应。
进行了这个界定之后,再看先秦诸子的学说,脉络就清楚了。
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抱负最宏大,对于“三位一体”的信念最坚定,天道、人伦和天人相与之际三端缺一不可,所以立志要修旧起废,从正面匡扶周道。如太史公所言:周道衰废,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论诗书,作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辩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王道之大者也。【4】
对于天人相与,儒家给的是完整解。《礼记•礼运》中表达得很清楚:
故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也。是故夫政必本于天,淆以降命。命降于社之谓淆地,降于祖庙之谓仁义,降于山川之谓兴作,降于五祀之谓制度。此圣人所以藏身之固也。【5】
以管仲商鞅韩非等为代表的法家,与儒家同出孔学,两派的区别在于:儒家的理想更高远,追求升平世到太平世之间的“大同”;而法家的关注点在当下,致力于据乱世到升平世之间的“小康”。所以,法家对于“三位一体”能否恢复其实半信半疑,虽然也相信天道,但执意将其中的道解成“法”和“纪”。《管子•形势解》:
天,覆万物,制寒暑,行日月,次星辰,天之常也。治之以理,终而复始。主,牧万民,治天下,莅百官,主之常也。治之以法,终而复始。【6】
《韩非子》:
道者,万物之始,是非之纪也。是以明君守始以知万物之源,治纪以知善败之端。【7】
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属于所谓“南派”,偏于逍遥,对于“三位一体”的信念最淡漠,不认为圣贤们能够做什么。于天道、人伦和天人相与之际这三端,只信天道,只解无为,根本不相信人伦。所以老子会主张“绝圣弃智”、“绝仁弃义”:
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道则不然,损不足,奉有余。…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8】
庄子也说:
夫帝王之德以天地为宗,以道德为主,以无为为常。…当是时也,阴阳和静,鬼神不扰,四时得节,万物不伤,群生不夭,人虽有知,无所用之,此之谓至一。【9】
以墨翟禽滑厘为代表的墨家,属于北南之间的“宋郑派”。但墨子鲁人,习孔子之书,业儒者之业,在匡扶周道的事业上与儒家算是同志,对于“三位一体”的信念同样坚定。墨家于天道、人伦和天人相与之际这三端,比儒家更为相信人伦的力量,也相信天人相与。对于天道,执意要解出“天志”。《墨子•法仪》曰:
然则奚以为治法而可?故曰:莫若法天。天之行广而无私,其施厚而不德,其明久而不衰,故圣王法之。既以天为法,动作有为,必度于天。天之所欲则为之,天所不欲则止。然而天何欲何恶者也?天必欲人之相爱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恶相贼也。奚以知天之欲人之相爱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恶相贼也?以其兼而爱之,兼而利之也。奚以知天兼而爱之,兼而利之也?以其兼而有之,兼而食之也。【10】
所谓诸子百家,就其“大宗”而言,就是以上几家,其他诸家都是“大宗”之间混合衍生而成,不再一一详述。本文对此进行梳理,旨在特别强调这些产生于那个特殊时代的古典学说与“天下”型定居文明本身以及这个文明内在困境之间必然的和因果的联系。今天的中国,正在大步跨入新时代,面对传统思想和文化的继承和借鉴问题,更需要对这些联系进行清晰的辨识。
70年对话5000年,新时代所达到的高度越高,前景越远大,对于历史的追溯和探究也越深越远。笔者才疏学浅,力有不逮,在此抛砖引玉,诚邀学界同仁共襄此举。下一篇“三千年来中国人的政与商”。敬请关注。
参考文献:
1、见《史记》、《资治通鉴》等
2、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
3、同上
4、见《史记•太史公自序》
5、见《礼记•礼运》
6、见《管子》
7、见《韩非子》
8、见《道德经》
9、见《庄子》
10、见《墨子》
本文系观察者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相关文章
-
三巴龙:中国四川小型食草恐龙(距今1.5亿年前)
-
古代遗物中的一钉一瓦都宝贵|纪念郑振铎诞辰120周年
-
晚清老照片:王妃与小妾貌美惊艳温柔如水,壮汉在山野奋力耕地!
-
元朝为什么能征服西藏
-
中国首位跳伞女兵马旭被授予“冰城楷模”
-
在红军长征的队伍中,这位女兵最特殊,也走得最艰难
-
历代端午节的习俗有哪些?汉朝人为何将五月初五视作“恶日”?
-
古墓出土一件文物,专家:这项工艺原来不是印度的,是我们自创
-
揭秘甲午海战清军装备:炮内装沙子并非腐败而是另有大用处
-
虢国夫人和杨国忠什么关系?远方堂兄妹竟然有私情
-
重游国家博物馆
-
银牌天使、宇宙大将军,古代这些奇葩官职都是干什么的?
-
小雪节气的含义是什么,雨雪纷飞(每年的11月22-23日)
-
清廉学校|共和国三位总理的廉洁故事
-
黄永胜被判刑入狱,他的妻子为何安然无恙?并且官职越当越高
-
历史上的故宫建筑为何频发火灾?
-
推背图是谁写的:相传为李淳风袁天罡所写(历代不断修改)
-
无畏摩罗斯龙:霸王龙的迷你祖先(体长仅3米)
-
【百年党史·天天课堂】党史上的今天·10月24日
-
缙云甲龙:早期唯一带尾锤的甲龙(宽达45厘米)
-
虐龙:北美大型暴龙类(长9米/牙齿多达64颗)
-
军阀何键打不赢红军,作出了一个丧尽天良的决定
-
俗语:“男怕摸头,女怕摸腰”,为何有此一说?一文告诉你
-
关于红楼梦黛玉葬花 黛玉葬花有什么寓意
-
慈安死亡之谜:慈禧丑事败露为自保毒死慈安?
-
西安事变后周恩来的四次历险
-
蜡笔小新与大头儿子谁家更有钱,结果更偏靠蜡笔小新
-
三星堆何以让人称绝
-
【边疆时空】王义康|唐代周边内附诸族赋役问题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