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大教授商伟忆恩师:与林庚先生相处的日子
知道林庚先生,是因为一首小诗:
“
冬天的树林像野鹿的角
太阳的四周春天又来了
刚化了的河水透着多么蓝
泥土里的气息带微微的潮
”
当时只对这古今杂糅的文字心生惊艳,却未去深究。直至因《给孩子的古文》的作者商伟而重新认识这位带着名士遗风的大家时,才知斯人已于十余年前故去……
初读《给孩子的古文》中商伟先生的文字,颇为其间自然流淌的古风惊讶,而见到本尊时,也曾讶异他殊异于时人的儒雅气度。及至读到《与林庚先生相处的日子》,才恍然大悟,真实感知到这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而产生的神奇化学作用。

林庚
(1910—2006)
字静希,原籍福建闽侯,生于北京。现代诗人、古代文学学者、文学史家。1928年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1930年转入清华大学中文系。北京大学教授。

商伟
1962年出生于福建,曾先后毕业任教于北京大学、哈佛大学,现为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教授,著有《给孩子的古文》。在北大任教期间曾兼任林庚先生的助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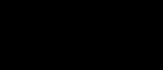
与林庚先生相处的日子
○
商 伟
一九七八年十月,我离开福州,开始了在北京大学十年的生活。一九七九至一九八○学年,第一次听林先生讲课。记得那是在第一教学楼二层的一间教室,课的名称是“《楚辞》研究”。这门课对我的影响,多年后我才明白。
这是一门选修课,内容包括先生正在撰写的《天问论笺》。先生用了好几堂课的功夫讲解《天问》的考证和错简的问题。我对《楚辞》学一无所知,听起来当然像天书一样困难。不过,先生化繁为简,举重若轻,竟然将考据和笺注这样的题目讲得引人入胜。先生说:我们固然不是为考据而考据,可是考据的问题又总是无法回避。考据并不意味着钻故纸堆,闭目塞听。好的考据家就像是出色的侦探。我们每天上课下课,走的是同一条路,可是对周围的世界,或者视而不见,或者熟视无睹。如果福尔摩斯也从这条路上走过,他的观察就和我们不一样。他能在我们熟悉的事物中看出问题。任何细微的变化,哪怕是蛛丝马迹,也逃不过他的眼睛。他甚至凭嗅觉就知道发生了什么。这种锐利的直觉和发现问题的能力,是侦探的职业敏感,也是考据家的第一要素。
先生的话引起了我们对这门学问的兴趣。年轻的大学生谈起考据就想到坐冷板凳,皓首穷经,因此视为畏途,避之惟恐不及。可是说到侦探,有谁不跃跃欲试,仿佛唾手可得?其实,这两门行当,如果不是旗鼓相当,至少也可以触类旁通。不论是侦探还是考据,都需要耳聪目明;推理之外,还得有洞察力和想象力。我后来才知道,先生的这几句话也同样适用于诗人和学者,更是他本人的写照。先生治《楚辞》学,并没有被历代浩如烟海的注解所困扰和迷惑,而是目光如炬,从诸如《史记》的《秦本纪》这样常见的史料中发现了诠释《天问》的线索。此外,先生快刀斩乱麻,处理了一向众说纷纭的《天问》错简问题,又在它的不相连贯的问话体的文字中理出了历史兴亡的主题脉络。这些考据的难处和好处,当然都是我当时体会不到的。

1933年,林庚清华大学毕业照
二十多年以后回想起来,先生的讲课留给我最深刻的印象是他诗人的气质和风采。先生身着丝绸长衫,风度翩翩,讲课时不读讲稿,只是偶尔用几张卡片,但是思路清晰,且旁征博引,让我们一睹文学世界的万千气象。讲到《九歌》中
“帝子降兮北渚,目渺渺兮愁予。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
和宋玉《九辩》的
“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
如何开了悲秋的先声,将汉魏数百年的诗坛笼罩在一片秋风之下,又怎样余波袅袅,在此后的诗文歌赋中不绝如缕,先生用的几乎是诗的语言,而他本人便如同是诗的化身。
我记得当时我们完全被征服了。全场屏息凝神,鸦雀无声,连先生停顿的片刻也显得意味深长。这情景让我第一次感受到诗的魅力和境界。一九八二年本科毕业之前,我决定报考中国古典文学的硕士研究生,师从林先生的弟子袁行霈先生,专攻魏晋南北朝隋唐诗歌。

2002年,林庚教授(中)与袁行霈教授(右)
先生的“《楚辞》研究”是退休前最后一次为本科生授课,是先生告别讲坛的仪式。在听众中,经常可以见到当时系里的一些老师。大家心里都明白,这是一个时代的结束。我得以亲历其境,当然深感荣幸,不过荣幸之余,又不免有些担心,因为期末得交一篇论文。我煞费苦心炮制的那篇文章,细节已记不清楚了,题目好像是《从离骚中的龙与马谈起》。《离骚》讲述上下求索的旅程,刚刚说到“驷玉虬以乘兮溘埃风余上征”,却又说“饮余马于咸池兮总余辔乎扶桑”。终篇前的一节也同样是以“龙”开始,及至“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则“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有的注家觉得这前后的变化殊不可解,于是引证《礼记》“天子乘龙载大”一句,又引郑玄注“马八尺以上为龙”,以为这样便一劳永逸地解决了“龙”“马”之间不相一致的问题。我以为这一说法胶柱鼓瑟,大煞风景,于是慨然命笔,指出《离骚》中的“龙”“马”之变与诗中的想象逻辑及情感律动正相合拍。展望前程,意兴飞动,诗人便“驾飞龙”“驷玉虬”。徘徊眷顾,怅然失意,则龙的形象便为“蜷局不行”的马的姿态所替代了。屈原所想象的天上的行旅,绝少受物质世界的羁绊,在诗歌的语言上也更倾向于抒情的跳跃而非叙述的连贯。由此创造了一个诡异变幻的想象空间,如同是中国戏曲舞台的虚拟背景,任凭演员呼龙唤马,御风而行,虽朝发苍梧夕至悬圃,亦无不可,而龙马之变,又有何妨?
文章交上去不久就发了回来,我的成绩是A!那一年我不过十七岁,于古典文学尚未知深浅,因此,兴高采烈之余,竟有些踌躇满志了。学期结束后,有一次又听先生的助教钟元凯说,先生以为文章写得不错。这当然更让我大喜过望。曾经想去拜访先生,可是事出无因,未免唐突,终于也就作罢了。
一九八四年底,我获得了中国文学的硕士学位。在此之前的几个月,听袁先生说,系里在考虑安排我留校任教。有一天,元凯忽然来敲门,问我是否愿意在任教之外,接替先生的助手工作。系里也有类似的考虑,不过,先生希望先见一面。几天后的一个晚上,在元凯的引导下,我第一次走进了燕南园六十二号。那天室内的灯光略显暗淡,可是在我的印象中,先生兴致很高,问了我的年龄后,大笑说:“我们之间隔着半个多世纪!”就这样开始了我与先生相处的三年多的珍贵时光。

燕南园62号院
因为我刚刚开始教书,助手的工作耽搁了一段时间才真正起步。不过,很快我就发现,为先生做事,和先生聊天,是相当愉快的经验。按照当时的日程,我们每周见一次面。首先是整理出版《唐诗综论》。其中的文章大多已经发表,只有两篇得从头开始。一篇是《唐代四大诗人》,另一篇是《漫谈中国古典诗歌的艺术借鉴》。先生因为常年手颤,书写不便,我们的工作方式通常是先生口述,由我记录整理以后,读给先生听。如此往返几次,最终定稿。先生以治中国古典诗歌而闻名,讲论唐诗更是他的本色专长。记得先生每次说到唐诗,总是神采飞扬。若不是师母叫停,真的是欲罢而不能了。这些谈话留给我的印象,至今新鲜如初,仿佛唐诗的精神已经化作了先生的生命血脉,不必假以外力,反求诸己,即可呼之欲出。在我的理解中,诗与生活的融会贯通,水乳交融,不正是中国艺术的最高境界吗?
先生讲唐诗,以“盛唐气象”和“少年精神”闻名学界。而二者又都是出自对文学的直接感受,保留了丰富的感性的成分。先生论王维:
古人称王诗‘穆如清风’,那就仿佛是清新的空气,在无声地流动着,无时不有,无处不在。
(《唐代四大诗人》)
又引《同崔傅答贤弟》
扬州时有下江兵,
兰陵镇前吹笛声。
夜火人归富春郭,
秋风鹤唳石头城。
评论说:
仿佛是在最新鲜的空气中一路走来。他并不在描写具体场景,也不是记述行程和路线,而只是将一路上的感受写了下来,靠着沁人心脾的气息连贯为一体。
三言两语,却准确地把握住了王维诗歌中跳动的脉搏。这样的语言,新鲜明快而恰到好处,既不摆论文的架子,也全无八股的习气。借用后人评唐诗的说法,是“色泽鲜妍,如旦晚脱笔砚者”。也就是说,先生将唐诗批评提升到了唐诗的境界。


王维《长江雪霁图》
先生对文学的评论也有其智性和哲理的层面。他说:
艺术并不是生活的装饰品,而是生命的醒觉;艺术语言并不是为了更雅致,而是为了更原始,仿佛那语言第一次的诞生。这是一种精神上的力量。物质文明越发达,我们也就越需要这种精神上的原始力量,否则,我们就有可能成为自己所创造的物质的俘虏。
(《漫谈中国古典诗歌的艺术借鉴》)
在八十年代中期,这种声音听上去真有如空谷足音,而这又正是先生一贯的想法。早在一九四八年的《诗的活力与诗的新原质》中,先生就特为强调了诗的“原创性”。先生认为,诗的突破性在于它的全部力量凝聚在一个点上,如同光聚成焦点而引起燃烧。点的突破是一切创造性的开始。点延伸而有线,历史便是线的展开。然而,线性的历史终不免有所因袭,因袭的力量愈强,原初的动力就愈弱。艺术就是要克服这因袭的惰性:
我们都有这个经验,如果因久病住院,一旦病愈,带着一片生机走出医院时,看到眼前的一草一木就都会感到特别新鲜。因为使人感觉迟钝的习惯性被割断了一段,就又恢复了原有的敏感。这敏感正是艺术的素质。谢灵运‘卧疴对空林’之后乃出现了‘池塘生春草’那样‘清水出芙蓉’一般的天然名句,其所以鲜明夺目,就因为它生意盎然。
在我的印象中,先生对文学艺术抱有非同寻常的信念。这在今天这个物质过剩、精神匮乏的时代,大概不免要难乎为续了,然而也正因此而更加难能可贵。先生认为物质超出我们个人的需要,就成为负担。而物质的世界,一旦走进去就出不来了,因为物质有引力(别忘了先生早年是清华大学物理系的学生),结果我们每个人都不免像先生的一首诗中所写的那样,瞻前顾后,患得患失:
舍不得放弃一些于前
之后更忐忑于因此所失掉的
不能断然撒手的人
乃张皇于咫尺的路上。
在先生看来,艺术是一种更高的精神的呼唤。先生用火和光作比喻:是火就要燃烧。火是光的起源。然而,火又同时带来了灰烬,这光最后也可能就要消失在这物质的残骸里。因此,艺术要不断摆脱灰烬,这就是要在精神上不断为自己找回那个起点。先生赞美原始性,正因为那是一切开始的开始。
这些话显然已经不只是在谈文学和艺术,而是涉及了生活的态度和人生的境界。可是我们知道,先生的这种人生的哲学经受过多重的考验。的确,生活中的各种磨难,日常琐事,人事纠缠,政治运动,都足以让人意气消沉,窒息了生命的火焰。先生那一代学者经历了抗战期间的流亡,先生本人就曾在临时迁移到长汀的厦门大学任教。

1945年,林庚一家在厦门大学
师母回忆说,长汀的条件异常艰苦,动不动还得抱着孩子跑防空洞,躲避日军飞机的轰炸。在“文革”中,先生也照例吃了不少苦头,运动初期,被指派去打扫学生宿舍,家中的客厅又挤进了另一户人家,情形之窘迫,可想而知。后来师母多病,又近乎失明,先生悉心照料,每日心悬数处,真是谈何容易。可是先生多次说:“我这些年身体还可以维持,就是因为有一个好的精神状态。”而这又岂止是说说而已?真正的精神力量,并不需要叱咤风云,或表现为金刚怒目。
“文革”十年,是物质和精神双重匮乏的时期。不过,先生自有他对付的法子。在《西游记漫话》的《后记》中,先生说:
“
十年动乱期间,夜读《西游记》曾经是我精神上难得的愉快与消遣。一部《西游记》不知前后读了多少遍,随手翻到哪里都可以顺理成章地读下去,对于其中的细节,也都仿佛可以背诵似的。而已经如此熟悉了,却还是百读不厌,这或许正是《西游记》的艺术魅力所在吧。
”
至于厦大的那段经历,我只记得先生有一次说到,他在长汀的球友多少年后还从海外来看他,一起回忆当年“弦歌不辍”的日子。先生的豪爽和达观,于此可见了。
很早就听说先生对《西游记》颇有心得,只是从未见诸文字。闲谈的时候,先生偶尔提到他的一些发现和想法,我听了以后,在日记中连声惊叹“非同小可”。就像是说书,听了前一章,便迫不及待,想知道“后事如何”,我多次敦促先生赶紧开始。于是,从一九八七年的春天到一九八八年的七月,前后历时一年多,这篇题为《西游记漫话》的长文终于脱稿了。用先生《后记》中的话说,“这一段时光是愉快的,谈论《西游记》成了生活中的一大乐事”。这种兴奋愉快的心情也贯穿了全文的字里行间,仿佛一气呵成,得来全不费功夫。在先生的著述中,我尤其喜欢这篇文章,这当然也与我后来转向古典小说有关。我为研究生开中国小说的讨论课,规定学生必读,因为它太好读了,读过之后,让我们恍然大悟,知道学问原来可以这样做。所有为学术折磨得苦不堪言的学者,都应该读一读这篇文字,因为它提醒我们当初为什么会喜爱文学,又为什么要研究文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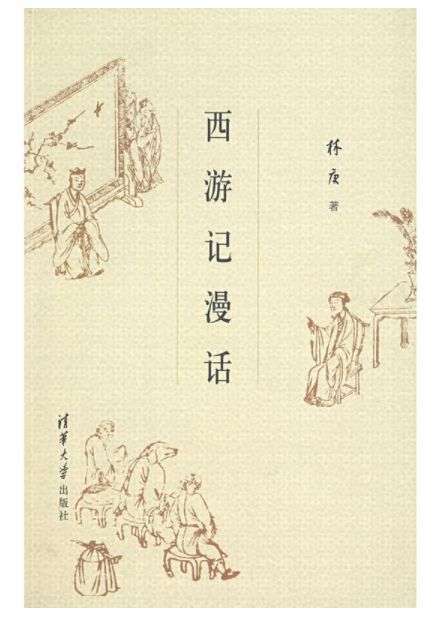
林庚《西游记漫话》
《西游记漫话》已经再版,它的好处,读者自有判断。我所感兴趣的有两点:一是先生善于从文学作品中发现问题,并且在不同类型的文本之间建立联系。前者需要敏锐的眼光和判断力;后者更多地依赖运思的巧妙。……我们研究《西游记》,向来只提及上古的神话、中古的志怪传奇,稍晚的《封神演义》,极少想到“三言”、“二拍”和《水浒传》,因为“神魔小说”的定义就像孙悟空给唐三藏画的那个圈子,把我们的想象给限制住了。跨出这个圈子,我们并没有被妖怪拿去或者吃掉,而是看到了一个新的天地,听见一些遥远的话语,声息相通,如相应答,向我们讲述一个从未听说过的故事。
协助先生撰写《西游记漫话》的另一点感触是,先生在以上论述的基础上,笔锋一转,进而指出《西游记》的想象力和喜剧性如何最终统一升华为一种童话精神。关于童话或儿童文学的问题,五四学者如周作人等,均有所讨论。当时的基本思路是通过与西方文学的对比,反过来问中国文学或者中国文化缺少了什么。比如说,中国为什么没有神话和史诗,或者至少是没有系统记载的神话和充分发展的史诗?中国的戏曲为什么晚出?也有人问为什么中国没有童话,为什么中国文学中儿童的形象如此罕见,而动物一旦开口说话就变成了妖怪,哪里还谈得上欧洲童话中那些可爱的王子公主呢?依照这种思路,接下来的诊断很可能就是中国文化又出了一个老大民族可以预想的毛病,那就是,我们的传统教育扼杀了儿童,窒息了天真的幻想等等。周作人因此着意于介绍欧洲的童话,或者从中国通俗或口头的文学中去探寻童话的消息。
现在看来,这些问题并不简单。自从一九六○年法国学者Philippe Ariès出版了他的名著Centuries of Childhood以来,不少学者认为,在欧洲的语境中,童年(childhood)是一个现代的概念。生长在中世纪欧洲的儿童与成年人穿的是一样的衣服,打一样的工。像成人那样不识字,因此也像成人那样受到口头文学的影响。毫不奇怪,儿童即便偶尔出现在中世纪的文学和绘画作品中,也不过是小大人的形象。童年既然是现代的产物,欧洲童话的观念也不免要有相应的调整。事实上,近三四十年来,欧美学者对格林童话的来源和性质已经提出了质疑,指出其中的不少作品并非如格林兄弟声称的那样来自民间的口头传说,而是出于作者本人的创作。而在十八世纪的法国,为儿童讲述的故事,在今天的读者看来,甚至包含了不可思议的、令人恐惧的、至少也是儿童不宜的内容。因此,追问中国的传统文学何以没有产生童话,从一开始就可能是一个错误。而如果从晚明的《西游记》中竟然可以确认某些童话的因素,则又不啻是一个重大的发现,不仅可以修正我们理解童话问题的习惯的前提和出发点,而且有可能由此而提出一系列新的问题供我们思考和讨论。
先生在《西游记漫话》中,从动物王国、儿童的游戏性与模仿性、天真的童心、非逻辑的想象与不连贯的叙述等方面,来描述弥漫在《西游记》中的童话气氛。这是文章中最精彩的部分,最能见出先生的童心和慧眼。例如第三十三回写孙悟空在平顶山与小妖换宝贝,先生评论说:
这一场戏是孩子气十足的。儿童好奇心重,总是看着别人的东西好,所以也就最喜欢交换。孩子们碰在一块儿,各自带来自家心爱的东西,像什么邮票、糖纸、烟盒,甚至拾来的石子、贝壳等等,拿出来夸耀一番,然后相互交换。怕事后翻悔,又赌咒发誓。这原是儿童生活中常见的场面,我们读来并不陌生。甚至连孙悟空与小妖的神情语吻也似曾相识,比如孙悟空听伶俐虫说要换宝贝,心中暗喜道:“葫芦换葫芦,余外贴净瓶:一件换两件,其实甚相应!”即上前扯住伶俐虫道:“装天可换么?”那怪道:“但装天就换,不换我是你的儿子!”这一段对话读下来,就如同是在看一场儿童的游戏,神情姿态,直是毕现无遗了。
论述孙悟空在狮驼洞与老妖周旋的那一段文字也同样妙趣横生:
孙悟空能跑到妖怪的肚子里,这本来就只有童话才想得出,而他在妖怪的肚子里竟然又打秋千,竖蜻蜓,翻跟头乱舞,简直就像是一个无法无天的顽童。”小说接着写孙悟空出来以后,却还将绳子系在妖怪的心肝上,用手牵着,直扯着妖怪漫天里飘荡:“众小妖远远看见,齐声高叫道:‘大王,莫惹他!这猴儿不按时景:清明还未到,他却那里放风筝也!’”先生评论道:“不仅孙悟空在游戏,在小妖眼里,这一场搏斗也正有如放风筝的游戏了,还埋怨说‘不按时景’。这真正是一种儿童的兴趣,恰好可以说明《西游记》中追逐格斗的游戏性质。”
总之,《西游记》中的小妖常常好戏连轴,而在先生看来,他们有时竟像是一群天真烂漫的快乐儿童。若以常情度之,上述的场景和对话简直是无理取闹。而这正是它们的好处,因为它们讲的是儿童的道理。这样一个观察的角度,在我们的《西游记》研究中,实在不可多得。因为我们好大喜功,一心一意要在文本中寻找微言大义,仿佛不如此,就对不住这部小说,而这部小说也就因此不够伟大了。于是,我们轻易地放过了小说中这些神来之笔,忘记了小说之所以吸引我们,并不是因为它的宗教框架,而所谓西行取经通常不过是一个方便的借口,为的是让这里所读到的精彩游戏,连番登场,层出不穷。
先生谈到小说第七十四回中小妖“敲着梆,摇着铃”的一段文字时,提到丹麦童话作家安徒生的《火绒箱》中曾经这样写一个走在路上的士兵:
“
一个兵沿着大路走来——一,二!一,二!他背上有个背包,腰边有把腰刀,他从前出征,现在要回家去了。
”
先生说:“这个‘一,二!一,二!’用安徒生自己的话说,就是‘照着对小儿说话一样写下来’的。”
安徒生的这段话,用的是周作人当年的翻译。可见,先生对《西游记》的思考,虽然完成于八十年代,其中的问题,却可以追溯到他的青年时代。
写到这里,我不禁记起先生关于治学的一些谈话。在我离开北京前的一个月,先生郑重地谈到我将来的学术发展:
像你这个年龄是最可宝贵的。重要的是培养你自己的职业敏感和良好的素质,这样才有突破力。就像一把刀子是锐利的,遇到问题,可以迎刃而解,不论进入哪个领域,都能做到游刃有余。人不可能把材料都收集全了才开始研究,追求真理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发现的过程。就像侦探总是顺藤摸瓜,科学家从苹果落地这个事实中探索地心吸力的原理。这是别人都做不到的。别人也看到了这些现象,可是只有他才创造了地心引力说的理论。这种在常见事物中独具慧眼的能力,是一切发明创造的前提。
谈到写文章,先生反对铺陈,因为铺陈只是在面上展开。最重要的是要有纵深,要从一点深入进去,把问题说透,这样才能获得一个高度。严羽说:
唐人与本朝诗,未论工拙,直是气象不同。
这是一个境界高下的差别。而对于每一个人来说,这个敏感性的高度是在青年时代获得的,此后发展的规模取决于这个高度。所以,必须首先去发现自己的敏感点,找到自己的突破口,全力去培养它,发展它。
先生多年前的这番话仍然时常给我以醒觉,提醒自己不要被汗牛充栋的书本压垮了,淹没了,或者因为日常的事务而变得迟钝平庸,消磨了锐气和想象力。我更忘不了先生曾经这样说过:
无论什么样的学问,都应该高屋建瓴,也就是要保证在高水平上进行。就像是唐诗,工拙姑且可以不论,毕竟气象不同。这气象便是一个人的综合素质的体现。
与先生谈话,总是这样感到精神振奋,仿佛蓄电池又一次充电。而与先生相处,又每每有如沐春风之感,令人神清气爽。先生是诗人,可是先生说,诗人是一场修炼。先生对学术有自己的标准,却从不固执己见,更不落于迂腐;性情豪爽豁达,而又重人情讲事理;无论是日常平居,还是接人待物,都流露出淳厚的性情修养和文人本色。
一九八八年七月的一天,我上午刚刚在先生那里协助完成了《西游记漫话》的《后记》,下午又收到先生托保姆转来的一个便条:见条后即来一晤为感。我匆匆赶到燕南园,一进门,先生就拉着我的手说:有一件事情,你无论如何得答应我。我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才是。先生说:你上午说机票涨价,我不清楚到底涨了多少。这是三百元钱,你就用来买机票吧。我这才想起来,上午说到等出国签证期间,我打算回家一趟,顺嘴提到了机票的事情。我有些措手不及,又后悔上午多说了一句话,连忙说,我已经决定买火车票回去了。先生坚持说:不管买不买机票,这钱反正你是需要的,买衣服,置行装,都需要。我们相处了这几年,真舍不得你走!可是不知道怎样来表达才好。这种方式当然未能免俗,可是清高不解决问题。你现在有困难,我就应该帮助你。好在这是我们的一场情谊,不在乎方式。

燕南园62号大门
一个月以后,我离开了北京。此后的几年中,我一直与先生保持通信联系。也曾经多次打算回去看看,可是由于各种原因,直到一九九六年才终于成行。一九九七年和二○○○年,我又先后两次踏上了燕南园的小径。先生的书房仍然是当年的样子,连摆设也几乎没有变动,一切都让我那样惊讶地感到熟悉,恍惚之间,如同回到了过去。墙上挂着师母的相片,默默之中,含笑注视着我们。阳光透过窗前的竹叶洒落在案头,我和先生像从前那样各坐在书桌的一边,随意聊着,仿佛是继续昨天的谈话。周围的世界渐渐隐入背景,离我们远去,只有空气中的微尘在阳光下闪烁。在这相对晤语之间,十年的时光已悄然流逝!

林庚先生
记得一九八八年初,我陪先生去校医院检查身体,医生告诉我说,先生的脉搏和心跳像年轻人那样健康有力。他用的是诗的语言,说先生有一颗年轻的心。我想,我们比他更明白这句话的意思——无论是读过先生的文章,还是听过先生的课。我姑且就借用这句话来结束这篇文字,并从大洋的另一端,为先生祝福。
二○○四年十月于曼哈顿
文章原载《读书》2005年第02期
HOTRECOMMEND
/荐/读/

《给孩子的古文》
商伟 编注
策划出品:活字文化
中信出版集团
2019年04月
一部好的古文选,就是一部中华传统文化的读本。读一本好的古文选本,也就是经历一次古典文化的精神洗礼。
知名学者商伟主编的《给孩子的古文》精选从先秦到近代的古文八十篇,内容既有诸子百家之言,如《老子》《庄子》等篇章,也有史传篇目;既有脍炙人口的唐宋八大家散文,也有历代学者名家的精彩论断。书中古文言简意丰,有古人充满哲理的对话记录、朋友间寄思怀远的感情抒发,有古代名家对历史、人生、艺术的思考感悟,还有长辈的谆谆教诲,篇幅长短不一,读来朗朗上口,有助于从小培养古典文学素养。编者更添加了细致的导读和注释,既展现出古文写作的千姿百态,也启示阅读古文的不同方式,帮助读者深入理解文本。选本内容不仅适合孩子们课外阅读,也适合家长和孩子一起进行,共享阅读的喜悦和交谈的快乐,帮助孩子养成终生读书的习惯。
相关文章
-
龙女被逐出龙宫后拜观音门下
-
黄狮精和九灵元圣的关系,黄狮精是九灵元圣的干孙子
-
夜读丨人是否有贵气,要看这6点
-
洪七公这样的武林高手喜欢传授武功,为什么很少收徒弟?
-
黄帝和蚩尤的决战中原 五千年前的涿鹿大战
-
西天取经就是一场戏,众神皆知而不语,唯有这位大神坦言相告。
-
老子一气化三清是怎么回事?三清都有谁
-
详细分析悟空大闹天宫时不让二郎神出场的原因
-
巴布亚新几内亚游记-参加授勋仪式
-
契丹先祖起源的神话故事 流传着一个美丽的神话
-
西游记中的火焰山在哪里 吐鲁番北边(山顶最高温度八十多度)
-
豆瓣评分8.7,这个“新哪吒”不一般|《哪吒之魔童降世》影评
-
影院7月20日起有序复工《流浪地球》《战狼2》《美人鱼》等将复映
-
古代民间关于吕洞宾的神话传说 也是数不胜数
-
西游记中神仙究竟会不会死?他们的寿命并非永久,要靠技能来维持
-
黄道十二宫之处女座:德墨特尔的故事
-
獬豸为什么象征着法律?獬豸的寓意是什么?
-
十二金仙为什么入佛门 十二金仙为凡人做出了什么贡献
-
简单走心的句子,经典至极,说进心坎里!
-
九头鸟是否存在 九头鸟到底是什么动物
-
燃灯佛祖念个咒语就能降服大鹏雕,如来佛祖因何还请来诸佛菩萨?
-
菩提和如来谁的实力更强?如来册封孙悟空时,说出了两人的差距
-
西游记中孙悟空最威风?且看二郎神干的这六件事,媲美大闹天宫
-
半兽人是否存在 欧洲成功制造首批人兽混合胚胎
-
玉鼎真人是孙悟空师傅吗 宝莲灯中是孙悟空师傅(实际上不是)
-
鼍龙是哪位龙王的儿子?泾河龙王(最后被魏征梦中斩首)
-
秋季到港城来看雨
-
因美貌被西游记导演一眼相中,被张纪中拉去救场,成全片最大亮点
-
四根定海神针分别是什么 四根定海神针的来源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