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度历史图书选摘|中国乡村
撰文:萧公权
翻译:张皓、张升
东方历史评论编辑部评选出15部图书作品为“2018年度历史图书”(点此查看榜单)。我们在春节期间陆续刊登获奖作品选摘。祝各位读者新春愉快! |
萧公权先生以《中国政治思想史》闻名已久,多数大陆读者却在2018年才得观其另一部学术代表作:《中国乡村:论19世纪的帝国控制》(九州出版社)。尽管这本书英文版已面世几十年,但其中的问题意识和分析、判断并没有因此失去重要意义。
本书考察了19世纪清王朝统治中国乡村的政治体系,特别是国家控制乡村的统治,其中既有物质层面,也描述了清政府如何对农村进行思想控制。这种控制的合理性、效果以及乡村的“回应”,构成了本书核心内容和精彩所在。
乡村与城市、底层民众与政治精英的互动和关系变迁,可谓理解中国历史与当下的一种重要视角,过去如此,将来仍将如此。在此方面,此著将持续提供参考和启发。
以下文字选自该书第八章:宗族与乡村控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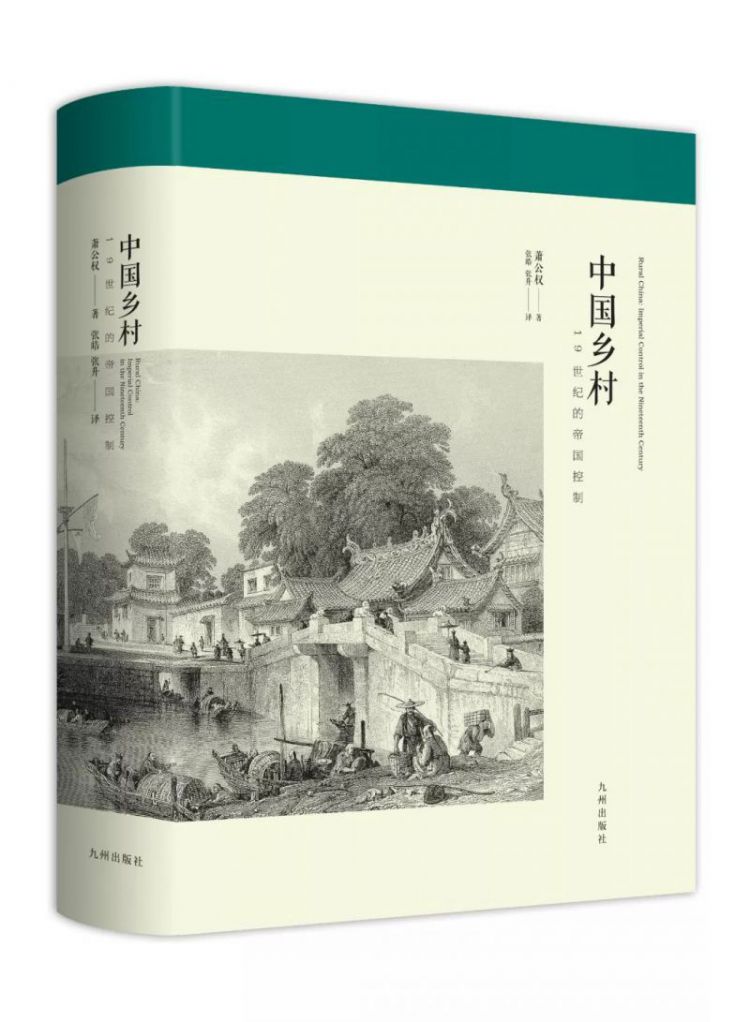
宗族的存在给乡村带来了一种凝聚力,这是其他因素所无法提供的。由于这一原因,对清政府来说,宗族是一个非常有用的乡村控制工具,但如何控制宗族本身,也给清政府提出了一些难题。本章的主要目的就在于讨论宗族组织在清王朝乡村统治体系中的地位。不过,我们首先必须探讨宗族本身的结构和功能。
“族”基本上是一个血缘群体;但自古代以来,它就在一些地区落地生根。近时一位学者指出,“‘族’是一种社会组织,拥有一个共同祖先,定居于特定地区或相邻地区”。
族最初定居之地区,可能是市或镇,但更多的是,它从乡下的一个点发展成为一座完整的村落。事实上族经常在乡村地区得到充分发展,乡村的形成常常取决于宗族的发展情况。虽然村社并不总是宗族定居的产物,但是宗族出现所带来的凝聚力,比其他因素可能带来的凝聚程度都要高。根据一位近代西方学者所说,在许多情况下,“除了那些以经济地位为基础的群体外,所有村内群体都直接或间接由宗族关系决定。……邻居主要由同一宗族的家庭所组成”。在这种情况下,把宗族视为“村落的中坚”,无可非议。
宗族和乡村之间关系密切的原因很简单。乡村里占大多数的农业人口,不像城市居民那样容易流动。因此,血缘纽带在乡村中比在城市中保存得要更好。这样,城市中的社会组织和乡村中的社会组织,其形式各不相同,前者以行会组织和“市民”组织为典型,后者以宗族组织为特征。
19 世纪的一位西方学者把乡村的形成描述为宗族定居的结果:“不知在过去什么时候,一些人户从其他地方迁移而来,修建房屋,成为‘当地居民’。……这就是村落。”这种情况或许在清帝国所有地区、所有时期都存在。位于直隶涿州的三坡(San-po)地区就是一个例子。这一多山的地区位于涿县东北边境上,在总面积为 55 里 × 30 里的地方上,分布着大小不同的 24 个村子;其中最大的村庄,人口不到 130 户。根据地方志的记载:
就其村多同姓,姓多同宗观察之,当初不过少数人家,因贫入山,私行开垦,日久渐成村落。
在特殊的社会环境下,会出现大规模的移民和定居。在这种情况下,不但可以了解定居的大致时间,而且可以了解定居的实际程序。四川省原住人口在遭到“流匪”大规模屠杀之后,于 17 世纪再次兴旺起来,就是一个能说明问题的事例。根据地方志的记载:
康熙时,招徕他省民以实四川。……始至之日,田无业主,听民自占垦荒。或一族为一村,或数姓联为一堡。……有一族占田至数千亩者。……然所占实不能尽耕也。
雍正时,四川总督宪德以入川人户繁多,疏请编保甲。……以一夫一妇为一户,户给水田三十亩,或旱地五十亩。兄弟子侄成丁者给水田十五亩,或旱地二十五亩。……得旨允行。于是各州县荒地以次开垦……至乾隆八年清查牌甲,共四千四百七十户,一万五千八百七十八丁。以四十里弹丸之地,阅时十三年,遽得此数。
偶尔也可能在某一特定地区追溯个别宗族的定居史。某些宗族的“族谱”或“宗谱”,就叙述了他们移民和发展的历史。一些地方志也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资料。从其中一部地方志所收集到的一些事例,可以进一步说明宗族村庄的形成过程。
广东香山斜排村谭氏宗族的“始祖”来自湖南衡州。1754 年,他和父亲来到香山。他的儿子定居斜排村;20 世纪早期,该宗族发展成为三大“房”,宗族成员超过两百多人。
广东香山县义门郑氏宗族的始祖,来自浙江,11 世纪担任广州知府。由于父子二人都葬在香山,所以后代子孙就定居香山,成为“香山开族祖”。到第八代时,有兄弟二人,分为两大房,二人为各房初祖,宗族人丁兴旺起来。其中哥哥(万四)的一房称为庞头郑族,其“九世祖”和濠头乡高氏宗族的女子结婚,并移居到那里。他的子孙一度达到千余人,其中虽然有一些在城市里经商,并聚集了相当财富,但大多数仍然留在乡下务农。弟弟(万五)的一房,又发展分成三房:(1)长子郑宗荣,有三个儿子(亦即第十代):郑谷彝、郑谷纯、郑谷纹。谷彝和谷纯一同迁到濠头,成为濠头分房之祖,后裔达 5,000 余人。(2)谷纹同他的父亲居住在钱山,因此成为钱山郑氏分房之祖,其后裔大约为 600 人。(3)郑宗得,郑宗荣唯一的弟弟,在 15 世纪早期担任过凤阳府和严州府知府。他定居鳌溪,成为鳌溪郑氏宗族的祖先,其后裔大约有 400 人。
陕西同官县王原王氏宗族的始祖,是山东督粮道,因犯渎职罪而被流放陕西。他和家人最初居住在同官城西 40 里的西古村,随后移居王家河村。他的一个后裔在 16 世纪得到举人头衔,并移居同官城。在 17 世纪,王氏宗族搬回乡下,定居王原;20 世纪初,该宗族成员大约 50 户,仍然居住在祖宗居住过的村子,即西古村、王家河村和王原村。
上述几个事例表明,移居者会定居某一地,并最终创造出一个族以及一个村落;或者,他会居住在某个乡村或城镇里,繁衍出一个族,而不是一个村庄。这种定居模式区别,部分解释了两种不同类型的宗族乡村,即“单族乡村”和“多族乡村”。在“单族乡村”里,居住着一些同姓家庭;在“多族乡村”里,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族比邻而居。

萧公权
在华南省区,“单族乡村”更为普遍。近代一位学者指出:
在过去六七个世纪里,迅速发展起来的家族,集中于华中和华南,也就是位于扬子江沿岸和福建、广东两省。在这些地区,许多乡村的居民完全是或主要是单姓家族的,他们之间存在着亲戚关系。……而在华北,绝大多数乡村是由不同姓氏家庭组成的。
一位西方观察者在19世纪的广东发现了下列情况:“同姓村民大体上居住在同村或附近;从始祖分出来的各房,就像榕树的分支一样,围绕着主干落地生根。”
19世纪另一位西方学者谈论了福建某个乡村的情况:“全村居民都姓林。显然是透过宗族制纽带联结在一起的。这种乡村里宗族制度是一种强大的结合。”在华北,很少见到单族乡村,那里的乡村常常是“一群家庭所组成,而非一个宗族”,或者说是由“经济独立的一群家庭,而非单一宗族”所组成。不过,中国北方的确也有单一宗族乡村存在,陕西《同官县志》的修纂者就记载说:“昔多聚族而居,故村庄多以姓名,如冯家桥、王家匾、董家河、梁家塬、李家沟等。”陕西《城固乡土志》也提供了下列一段资料:
国朝旧少土著,明季寇乱以来,自甘肃、四川、山西、湖北迁居者,一姓之民聚族于一乡,即以姓名其地。
不过,这样的事例相当少。以前由单一宗族构成的一些乡村最终失去了单一制的特点。19世纪的一位西方学者评论指出:“光阴荏苒,有时那些乡村赖以命名的宗族可能发生变化,以致再没有一个人留下来。这时,可能人们对有关变化情况的记忆已经消失,但乡村原来的名称还可以沿用至今。”
我们找不到统计数字来说明两种类型的乡村在清帝国各地的分布情况,但是下列一些数字虽然并不怎么精确,也可以描绘当时的一些情况。江西高安县(既不繁荣,也不贫穷)据载在19世纪中叶左右有1,291个村子,两种类型的乡村比例分配是:单族乡村1,121个,占87%;多族乡村170个,占13%。在广东花县,乡村总数为398个,不过比例与高安县不同:单族乡村157个,占40%;多族乡村241个,占60%。虽然单族乡村在华南也不必然占统治地位,不过其数量明显多于北方。现代一位学者发现,在直隶定州这个主要以农业为主的地区,在62个乡村中只有一个是单族乡村。虽然这或许不是决定性证据,但它可以支持一个总体观察结果,即在华北,大多数乡村是由不同姓氏宗族所组成的。
还应该指出的是,就像几个宗族可能居住在一个乡村里一样,一个宗族在子孙繁衍、最初家宅容纳不下之时,就会分散居住在几个村子里。陕西同官县杏林王氏就是一个极好的事例。在元朝末年(1367年),有位益王来到该村避难。他的后裔在明朝和清朝都以务农为主,到清末才有一部分人入学。这个宗族虽然没有什么家谱,但是对于居住在6个不同乡村的80多户族人,他们的宗族关系,历经几个世纪的岁月一直未遭到损害。
两种类型乡村性质的区别,反映在组织上的一些不同上。在单族乡村中,宗族和村社实际上是一致的,乡村头领就是宗族头领。比如,浙江宁波某个单族乡村,“选举”一名“长者”主持村社的行政事务,他同时又是族长,负责宗族事务。在清帝国其他地方也可以看到类似情况。而在多族乡村,情况有几分不同,族长虽然对村中事务产生一些值得注意的影响,但不一定就是村长。一个村社出现一个以上的宗族群体,宗族之间就会发生敌对或公开冲突;我们稍后会看到。此处值得指出的是,居住在一个村子的各个宗族之间,比起属于一个宗族的各个成员之间,并不存在更多的社会平等。正如一个宗族的绅士成员控制该宗族的普通成员一样,一特定村社里的一些宗族也会歧视其他宗族。他们的歧视可能建立在居住优势、人丁众多或自己宗族中一些成员拥有较高社会地位的基础上。即使在宗族组织相对较弱的华北地区,也可以看到这种现象。西方一位学者就指出,在一些乡村,“强调已被接纳的旧族成员的地位,歧视新近移居而来者,视他们为外人”。
在讨论宗族组织问题之前,设法对19世纪中国各地宗族发展的不同程度作一些解释,是很有用的。有些学者,如步济时,认为历史环境是一个决定性因素。他指出:
在华北地区,由于蒙古人和满人不断入侵,宗族制度的连续性遭到破坏,原来的宗族成员要么被杀害,要么被迫迁移南方。而在华南地区,由于远离这些入侵,因而宗族制度得到保留,各宗族在它们原来居住的乡镇和乡村里拥有更持久的住所。
这一看法很有道理,但作者应该进一步追溯到更早期的中国历史。早在蒙古人进入中原,随后在13世纪消灭南宋王朝之前,北宋王朝于12世纪前25年的崩溃就导致许多汉人宗族不得不渡过长江,移民江南。而且在更早的公元320年代,也有一场大规模移民南方的运动:西晋王朝崩溃后,一些望族移民江南,把许多汉族传统文化和社会风俗也带往那里。
经济情况也是导致移民的一个因素。现代一位学者认为,在华北经济不繁荣地区,宗族并没有什么重要地位;而在华北“农业发达地区”,宗族就拥有较大的影响。即使在华南,按照一些学者的看法,所有地区的宗族发展情况绝不相同:在广东、福建和江西,宗族势力较大;而在广东某些地方,特别是在“土沃而人繁”的地方,宗族的规模和实力就不是其他地区能够相提并论的了。屈大均在1700年的记述,描绘了下列图景:
岭南之著姓右族,于广州为盛。广之世,于乡为盛。其土沃而人繁,或一乡一姓,或一乡二三姓。自唐宋以来,蝉连而居,安其土,乐其谣俗,鲜有迁徙他邦者。
乡村的繁荣和强大的宗族组织之间的关系很容易理解。经济发展不达到一定程度,乡村就不能形成,任何规模的宗族也不能维持。如果很贫穷,就不可能有宗祠、祭田等等;而这些,对于一个要充分履行各方面职能的宗族来说,是很有必要的。陕西省一些地区的情况可以说明这种联系。根据地方志的记载,洛川、宜川和比邻地区大多数居民都生活在窑洞里。虽然也有一些小房屋,但都算不得什么财产。任何人都会想到,在这些贫穷地区,宗族组织是不存在的。按照另一地方志的记载,陕西同官县的情况是:“家族喜聚居……近因生活关系,析居者渐多矣。”
有时,地方经济的影响并不起什么决定作用。在陕西城固县,宗族采取减小规模、简化形式等方式存留下来。据说:
土著既少,谱牒无征,一族仅数十户,求如江南、广东之大姓,一族多至数百户,得姓受氏本末可考,则远逊矣。
同样的,陕西另一相对贫穷地区宁羌县,“客籍往来,多无定所。……其有入籍稍久,嗣续延长,宗支蕃衍,称为世家大族者……无由以考其世代源流。是亦谱牒之学久亡,而邑人又不讲宗法”。不过,即使在这些案例里,经济因素的影响也是比较明显的。
相关文章
-
二战日军罐头被保存,竟然还非常新鲜,专家给了两个字“保质”
-
追忆历史,激发情怀
-
红学是干啥的:研究《红楼梦》的(跨越多个领域)
-
【国学知识】鹿有什么象征意义,鹤在中国古代有什么地位?
-
历史上的和珅怎么死的?一生辉煌的和珅为何结局惨淡
-
唐宣宗的逆袭:登基前后判若两人,装疯卖傻36年,熬死5朝皇帝
-
荆轲是哪个朝代的人物:战国时期人物(因刺秦王失败而死)
-
这个国庆长假不无聊,12部国产高分纪录片推荐
-
No.1037陈壁生|“后经学时代”的经学
-
甲骨文将从隐学变为显学,已经不属于冷门和绝学,不会失传了
-
三国赵云老婆叫什么名字 三国演义赵云老婆是谁
-
赵云是怎么死的 赵云竟然死在妻子绣花针之下
-
所有汉人都梦寐以求的一颗头颅,被一个小兵砍下,保住欧洲四百年
-
九位抗日将领之死 八年抗战中让人动容的绝命书
-
这位中将当过南京军区政委,他的三个故事,都很感人
-
古代神秘消失的四大人物 李自成有人称他死于九宫山
-
文艺复兴时期有哪些文学代表作品
-
湘江战役是胜是败,我这样看!
-
黄继光牺牲后,他的母亲被毛主席三次接见,始终没有掉一滴眼泪
-
【党史百年·天天读】10月23日
-
大夏巨龙:中国最长的恐龙之一(长30米/距今1.2亿年前)
-
《天龙八部》“南慕容” 原型后燕开国皇帝慕容垂
-
凌烟阁第一功臣长孙无忌,权势滔天,却死在了亲外甥手中
-
巴金《团圆》的内容简介——《团圆》创作背景
-
【量化历史研究】制度自律者,得财政自由──来自殖民地墨西哥的证据
-
古代最聪明的三个人,智商逆天,刘伯温无缘上榜,第一名无人不知
-
历史解密古代有那些帝国称霸世界
-
30年前,在农村走街串巷的神秘“赊刀人”,为何预言句句成真?
-
他是铁匠出身的开国将军,在黑山一战成名,俘虏国军名将廖耀湘